王安:誰讓紀委受累?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4-04-11 0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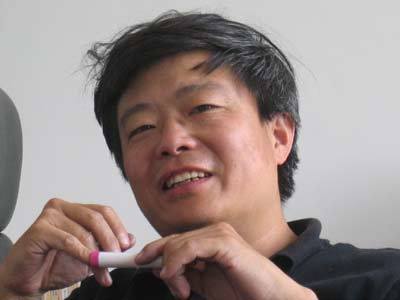
和訊專欄作者 王安(資料圖)
上文提了一句,“中紀委拿了副省長,還得操心村主任,很累。”這個村主任是平度市杜家疃村村主任杜群山。經警方4晝夜偵破,杜群山和承建商崔連國主使他人縱火燒死抗拒拆遷的護地農人耿福林,即“3•21”事件。
事件發生后,輿論一邊倒攻擊平度官方,諸如“五毒俱全”、“地方異化的標本”、“平度是不是法外之地”等,鮮有為平度官方辯護的。
以下摘錄的便是一則辯護,逐條反駁。由於護官的保護甚少,不妨多摘錄幾句——
“杜群山2011年通過民主換屆當選村主任,他的競選口號是不賣村里一分地。他並沒有違背諾言,涉事地塊5年前就已征收完畢,跟他沒有關係。有人向媒體爆料杜曾賄選,熟悉農村基層事務的人都清楚,這是農村選舉普遍存在的現象。
“問題恰恰出在這30%的收益分配上。1527萬撥付到村委賬戶后,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意見。辦事處希望村里能將錢存銀行或投資不動產、商鋪等,將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革,村民按年分紅,以防失地暴富后,因為不理性消費而返貧。而大部分村民希望一次性分光,少數村民也希望留存部分款項在村集體,用於綠化、硬化、修路、村辦幼兒園等公共支出。即使是一次性分光,也有不同聲音。村里婚喪嫁娶,人口不斷變化,從哪一個節點開始分,一直爭論不休。而被占的一百多畝地一直是包括李榮茂在內的幾十戶村民耕種,分錢的時候是全村平分還是這幾十戶多占?
“李榮茂本人的態度則讓其他村民很不理解。他不讓分錢,要地。如果分了這1500萬,等於認可了征地事實。而這塊土地8年前收歸國有,通過招拍掛賣給開發商,在村民看來程式上已然不可逆轉。李榮茂的底氣來自於2006年征地時的程式瑕疵——在當時的《放棄征地聽證證明》上,出現了兩個村民代表的鬼簽名,一個不存在,一個已去世。這個證據被曝光后,媒體和外界高度關注,將其視為平度征地程式不合法的鐵證。仔細一想這個根本不合邏輯。村委要找兩個聽話的村民代表,是很簡單的事,何必弄個鬼簽名授人以柄?唯一的解釋是,這是故意留下的瑕疵。
“對利益的訴求往往披上道德的外衣。李榮茂也成功的在媒體前樹立了保地英雄的形象。但是大多數村民私底下卻稱他為攪屎棍。村民之間的利益分配矛盾、農村的政治角力,遷怒於與此無關的施工方,最終讓耿福林老人獨自承受了衝突后果,7名縱火者鋃鐺入獄,面臨法律的嚴懲。”
民間的攻訐,對照上述這些辯護,讓旁觀者莫衷一是。有言稱“細節是魔鬼”,但在歷史的長河中,與“高層設計”相比,細節不論多么詳實、生動、耀眼,都是不重要的。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當官的無能當兵的跑斷腿”,都是這個意思。
那么,在平度案件中,是誰讓中紀委很累?其實,這個累死人的根子早就種下了,建國前后就注定了。
1949年12月,全國土改正烈,董時進卻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他認為: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多土地少,農村勞力剩余,應當節制生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土改后,失去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董時進的這些先見,大多已在今日得到印證,並在努力實施中。農村勞力正在向其他產業轉移,土地正在集中,改革前農民確實對種地失去熱情,等等。
董時進是中國少有的農業經濟學家,曾獲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之后多年研究、教授農業經濟,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校教授農業經濟,出任過江西省農業院院長,著述頗豐。並曾在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職。
農民的問題是公民權,農村土地的關鍵是產權。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的產權是明確的、可流通的;“富不過三代”,地主不是一個階級,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都能購買土地,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必須愛護而非打,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斗爭。將地主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沒收,分給貧農和無業游民,令這些收取不義之財者獲得暫時的好處,卻令他們失卻了良知,是對中國傳統道德的顛覆。在沒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礎的中國,傳統道德規範是社會整合之基礎。建議政府贖買大地主的土地,同時成立自耕農基金,扶持自耕農。
對於當時聖經一樣的“蘇聯經驗”,董時進批評說,“蘇聯的集體農場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單體或家庭式的農場好,是另一個問題。但我確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農業和最富的農民,都不是在蘇聯,而是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董時進指出:“這種制度(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完全是回復到封建和農奴制度,絕不是什么農民合作,擴大經營,提高效率的意思。”對中國土改,董時進說,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當年董時進建言時,明知土改大局已定,注定不被接受,但他還要說,結果只能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孤獨地遠走他鄉。
而以董時進之大才,啥都想到了,就是沒想到在今日土地交易中,出現了地方政府這樣一個大角色。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土地爆發式地溢價,地方財政對於土地嗜血般地依賴,使地方政府與握有所有權和承包權的農人變成對立關係。博弈雙方,一方握著公權力,另一方只能用腳投票,以命相搏。
而以我等有限的想象力,卻也沒有想到,土改並不是宣傳中的要讓農民翻身做主人,做公民,而是為城市做貢獻。劉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說:“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正是因為這種思路,中國可以流動的土地產權,被大躍進、人民公社徹底打爛,農人種田的熱情也被打爛。打爛了,打錯了,多少年后還得回過頭收拾,誰也拗不過真理。
盡管有紀委的勤勉善戰,但回頭收拾可就不容易了,仍難免會出現無數的平度慘案。平度農人說,牽走一頭牛,送回一只雞。而過去的歌曰:“豬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給咱親人解放軍。”
- 掌握全球財經資訊點我下載APP
文章標籤
上一篇
下一篇